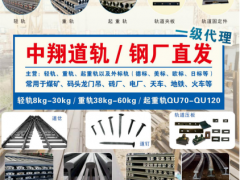我國大規劃的根底建設,5G等先進技能的集中迸發,讓工程機械有了大規劃的使用場景,因此也培育出一個強大的工業。我國工程機械工業開端了史無前例的快速追逐,并擠進了世界工程機械強國陣容。雖然還有許多“卡脖子”難題未解,但在第四次工業革命風起云涌的大布景下,巨大的我國工程機械工業迎來了邊開展邊重構工業互聯的前史重擔。
我國工程機械求解“卡脖子”難題
工程機械是“我國制作”的一張名片,許多設備可謂“大國重器”,其要害零部件“卡脖子”問題一向備受重視。筆者在“工程機械之都”長沙等地采訪了解到,近年來國內工程機械職業要害零部件的國產化率不斷提升,能夠“頂得上”,但部分高端零部件依然依靠進口,國產零部件離“用得好”還有距離。而跟著職業加速智能化、數字化轉型,控制器、傳感器等技能難題又擺在了企業面前,急需奮力求解。
國產零部件“頂得上”
坐落湖南長沙經開區的三一重工“18號廠房”,一派繁忙的生產景象。車間顯要方位展示的不是企業取得的榮譽,而是發動機、馬達、軸承、液壓件等各種要害零部件。工作人員說,這些要害零部件都是三一自己規劃、制作,而且完成了全面使用。
這是職業破解要害零部件瓶頸的一個縮影。事實上,工程機械職業很長一段時間存在“卡脖子”問題。以至于在2010年前,我國市場生產多少臺挖掘機,是由國外油缸企業決議,因為其時國產油缸密封性欠好、容易漏油,挖掘機所需的油缸只能依靠進口。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國內一些工程機械企業面對海外零部件供貨商停產、減少的嚴峻形勢,這再次對供應鏈安全敲響了警鐘。一家企業的負責人告訴筆者,去年6月,國外某品牌的汽車底盤斷供,主機廠不得不趕緊在國內尋找替代產品。
不過,這次危機并沒有真實卡住國內工程機械職業的脖子。在業內人士看來,這得益于近年來整個職業不斷加大研制投入,推動要害零部件的國產化,國產零部件在要害時刻能夠“頂得上”。
我國機械工業聯合會的分析稱,在國家“強基”工程的引導和市場需求的拉動下,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要害零部件完成了技能和規劃使用的重大突破,部分中心零部件“卡脖子”問題有所緩解。
以徐工為例,這家企業在“十三五”期間攻破的要害技能中,20%都是“卡脖子”技能。現在,徐工的起重機、挖掘機等主機完成了全型譜體系化配套,液壓件、傳動件、電氣件的克己率快速提升。
“要害零部件是一個投入大、短期內又難以見效的范疇,一旦被人‘卡脖子’,味道是欠好受的。”徐工集團工程機械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民說,現在,國內的許多研制效果現已到達國際先進水平,不少自主可控的硬核技能把握在自己手中。
自2005年以來,三一重工成立了10多家零部件公司,經過自主創新和協同創新對要害零部件進行研制及工業化。這家主機企業具有了不少“叫得響”的要害零部件,比方三一中興公司成為國內規劃最大、品種最多的液壓油缸生產基地之一,三一自產的發動機和底盤開端使用于工程機械和重卡。
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以為,要害零部件過于依靠國外,工業鏈就會很脆弱,這既是安全問題,也是成本問題。經過這幾年的盡力,三一的國產配置率不斷提高,提升了企業的整體競爭力。
向“最終10%”高舉高打
筆者了解到,盡管工程機械零部件取得了長足進步,但還存在“高端產品缺失、中低端產品同質化”的問題。高端液壓件、高端底盤、大噸位發動機等零部件進口量大,面對價格高、周期長、供貨不穩定等掣肘。
中聯重科副總裁孫昌軍以為,在中低端設備范疇,零部件逐漸完成國產替代,但部分高端要害零部件仍舊依靠從歐美日等地進口。當前,我國工程機械龍頭主機企業現已處于全球職業的第一陣營,一旦企業進入“高端競爭”“精品競爭”階段,就可能被“卡脖子”。
筆者了解到,因為材料、規劃、制作工藝等方面的距離,一些國產要害零部件的穩定性、可靠性、耐久性有所欠缺,導致客戶不敢試,主機廠也不敢用。比方,核電站吊裝需求特大噸位起重機,客戶對于國產要害零部件“心里沒底”,仍是得用國外產品。挖掘機被稱為“工程機械皇冠上的明珠”,因為其性能要求高,配置的發動機也許多是國外品牌。
此外,國產要害零部件還缺少創新,一些零部件停留在拷貝國外產品的階段。特別是前沿產品落后于人,比方汽車起重機的“單發”發動機便是由德國企業首要推出,國內企業再跟進學習。
王民以為,我國工程機械職業現已處理了90%的難題,但最要害的是要霸占最終10%,這就好像攀爬珠穆朗瑪峰的最終幾百米。我國工程機械工業中心零部件要向“高新優獨”上進取,必須“主攻高端、高舉高打”。
一方面,要重視根底創新。山河智能董事長何清華說,要突破高端要害零部件的規劃“門檻”,不是“運動式、砸錢”能處理的,而要精耕細作、埋頭苦干,鼓勵在某個方面有絕技的企業沉下心研制。對于單個主機廠研制零部件的投入太大、市場太小、不劃算的問題,能夠經過主機廠參與出資的基金引導,重點建設、扶持高端中心零部件企業,最終輻射整個職業。
另一方面,有業內人士主張在需求端學習新能源汽車扶持方針,補助終端用戶,引導和鼓勵國產要害零部件的使用,把市場真實培育起來,以處理曩昔國內產品不被接受而沒有辦法改善和迭代的問題。
探究智能轉型新課題
當前,工程機械職業加速智能化、數字化轉型,各大企業都在布局智能制作工廠,5G遙控挖掘機、無人起重機、無人壓路機、無人攪拌車等新式設備層出不窮。筆者了解到,傳統制作企業在智能化、數字化范疇的根底薄弱,從研制規劃到生產服務環節面對一些新的“卡脖子”問題。
湖南省工信廳配備工業處有關負責人說,本來制作業“卡脖子”的地方,首要仍是在某個中心部件,如發動機、液壓件,而跟著智能化升級,更重要的“卡脖子”問題是涉及高端精密加工的制作配備。
筆者在一家工程機械企業的智能制作車間看到,整個車間有上百臺工業機器人。技能人員坦言,在硬件層面,智能化產線、工業機器人許多“工具”需求從日本等國家進口;在軟件層面,數字化、智能化離不開“算法”,現在使用的大多仍是國外算法。
不僅如此,工程機械職業需求的仿真分析等工業軟件、被稱為工程機械“大腦”的控制器以及設備上遍及的傳感器,也許多需求進口。一家工程機械企業的研制人員說,控制器對可靠性要求很高,而國外企業不敞開控制器的“底層”(即與硬件匹配的驅動,相當于手機的安卓體系),國內企業受制于人,只能在其平臺上進行小使用的編程。
上述工信部分負責人主張,要大力推動短板配備攻關,引導企業充分利用數字化、網絡化技能,研制智能化配備產品。把提升智能制作供應才能放在更為突出的方位,加速突破智能制作中心配備及工業軟件體系,趕快補齊要害配備、根底零部件、體系軟件等短板。
業內人士指出,破解新的“卡脖子”問題,傳統制作企業不能單打獨斗,而要整合職業資源,構成才能互補、利益同享、危險共擔的工業生態圈。筆者了解到,有的企業已在和國內供貨商“齊頭并進”,探究構建智能化、數字化時代的協同創新模式。
(本文轉載自環球網)
我國工程機械求解“卡脖子”難題
工程機械是“我國制作”的一張名片,許多設備可謂“大國重器”,其要害零部件“卡脖子”問題一向備受重視。筆者在“工程機械之都”長沙等地采訪了解到,近年來國內工程機械職業要害零部件的國產化率不斷提升,能夠“頂得上”,但部分高端零部件依然依靠進口,國產零部件離“用得好”還有距離。而跟著職業加速智能化、數字化轉型,控制器、傳感器等技能難題又擺在了企業面前,急需奮力求解。
國產零部件“頂得上”
坐落湖南長沙經開區的三一重工“18號廠房”,一派繁忙的生產景象。車間顯要方位展示的不是企業取得的榮譽,而是發動機、馬達、軸承、液壓件等各種要害零部件。工作人員說,這些要害零部件都是三一自己規劃、制作,而且完成了全面使用。
這是職業破解要害零部件瓶頸的一個縮影。事實上,工程機械職業很長一段時間存在“卡脖子”問題。以至于在2010年前,我國市場生產多少臺挖掘機,是由國外油缸企業決議,因為其時國產油缸密封性欠好、容易漏油,挖掘機所需的油缸只能依靠進口。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國內一些工程機械企業面對海外零部件供貨商停產、減少的嚴峻形勢,這再次對供應鏈安全敲響了警鐘。一家企業的負責人告訴筆者,去年6月,國外某品牌的汽車底盤斷供,主機廠不得不趕緊在國內尋找替代產品。
不過,這次危機并沒有真實卡住國內工程機械職業的脖子。在業內人士看來,這得益于近年來整個職業不斷加大研制投入,推動要害零部件的國產化,國產零部件在要害時刻能夠“頂得上”。
我國機械工業聯合會的分析稱,在國家“強基”工程的引導和市場需求的拉動下,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要害零部件完成了技能和規劃使用的重大突破,部分中心零部件“卡脖子”問題有所緩解。
以徐工為例,這家企業在“十三五”期間攻破的要害技能中,20%都是“卡脖子”技能。現在,徐工的起重機、挖掘機等主機完成了全型譜體系化配套,液壓件、傳動件、電氣件的克己率快速提升。
“要害零部件是一個投入大、短期內又難以見效的范疇,一旦被人‘卡脖子’,味道是欠好受的。”徐工集團工程機械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民說,現在,國內的許多研制效果現已到達國際先進水平,不少自主可控的硬核技能把握在自己手中。
自2005年以來,三一重工成立了10多家零部件公司,經過自主創新和協同創新對要害零部件進行研制及工業化。這家主機企業具有了不少“叫得響”的要害零部件,比方三一中興公司成為國內規劃最大、品種最多的液壓油缸生產基地之一,三一自產的發動機和底盤開端使用于工程機械和重卡。
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以為,要害零部件過于依靠國外,工業鏈就會很脆弱,這既是安全問題,也是成本問題。經過這幾年的盡力,三一的國產配置率不斷提高,提升了企業的整體競爭力。
向“最終10%”高舉高打
筆者了解到,盡管工程機械零部件取得了長足進步,但還存在“高端產品缺失、中低端產品同質化”的問題。高端液壓件、高端底盤、大噸位發動機等零部件進口量大,面對價格高、周期長、供貨不穩定等掣肘。
中聯重科副總裁孫昌軍以為,在中低端設備范疇,零部件逐漸完成國產替代,但部分高端要害零部件仍舊依靠從歐美日等地進口。當前,我國工程機械龍頭主機企業現已處于全球職業的第一陣營,一旦企業進入“高端競爭”“精品競爭”階段,就可能被“卡脖子”。
筆者了解到,因為材料、規劃、制作工藝等方面的距離,一些國產要害零部件的穩定性、可靠性、耐久性有所欠缺,導致客戶不敢試,主機廠也不敢用。比方,核電站吊裝需求特大噸位起重機,客戶對于國產要害零部件“心里沒底”,仍是得用國外產品。挖掘機被稱為“工程機械皇冠上的明珠”,因為其性能要求高,配置的發動機也許多是國外品牌。
此外,國產要害零部件還缺少創新,一些零部件停留在拷貝國外產品的階段。特別是前沿產品落后于人,比方汽車起重機的“單發”發動機便是由德國企業首要推出,國內企業再跟進學習。
王民以為,我國工程機械職業現已處理了90%的難題,但最要害的是要霸占最終10%,這就好像攀爬珠穆朗瑪峰的最終幾百米。我國工程機械工業中心零部件要向“高新優獨”上進取,必須“主攻高端、高舉高打”。
一方面,要重視根底創新。山河智能董事長何清華說,要突破高端要害零部件的規劃“門檻”,不是“運動式、砸錢”能處理的,而要精耕細作、埋頭苦干,鼓勵在某個方面有絕技的企業沉下心研制。對于單個主機廠研制零部件的投入太大、市場太小、不劃算的問題,能夠經過主機廠參與出資的基金引導,重點建設、扶持高端中心零部件企業,最終輻射整個職業。
另一方面,有業內人士主張在需求端學習新能源汽車扶持方針,補助終端用戶,引導和鼓勵國產要害零部件的使用,把市場真實培育起來,以處理曩昔國內產品不被接受而沒有辦法改善和迭代的問題。
探究智能轉型新課題
當前,工程機械職業加速智能化、數字化轉型,各大企業都在布局智能制作工廠,5G遙控挖掘機、無人起重機、無人壓路機、無人攪拌車等新式設備層出不窮。筆者了解到,傳統制作企業在智能化、數字化范疇的根底薄弱,從研制規劃到生產服務環節面對一些新的“卡脖子”問題。
湖南省工信廳配備工業處有關負責人說,本來制作業“卡脖子”的地方,首要仍是在某個中心部件,如發動機、液壓件,而跟著智能化升級,更重要的“卡脖子”問題是涉及高端精密加工的制作配備。
筆者在一家工程機械企業的智能制作車間看到,整個車間有上百臺工業機器人。技能人員坦言,在硬件層面,智能化產線、工業機器人許多“工具”需求從日本等國家進口;在軟件層面,數字化、智能化離不開“算法”,現在使用的大多仍是國外算法。
不僅如此,工程機械職業需求的仿真分析等工業軟件、被稱為工程機械“大腦”的控制器以及設備上遍及的傳感器,也許多需求進口。一家工程機械企業的研制人員說,控制器對可靠性要求很高,而國外企業不敞開控制器的“底層”(即與硬件匹配的驅動,相當于手機的安卓體系),國內企業受制于人,只能在其平臺上進行小使用的編程。
上述工信部分負責人主張,要大力推動短板配備攻關,引導企業充分利用數字化、網絡化技能,研制智能化配備產品。把提升智能制作供應才能放在更為突出的方位,加速突破智能制作中心配備及工業軟件體系,趕快補齊要害配備、根底零部件、體系軟件等短板。
業內人士指出,破解新的“卡脖子”問題,傳統制作企業不能單打獨斗,而要整合職業資源,構成才能互補、利益同享、危險共擔的工業生態圈。筆者了解到,有的企業已在和國內供貨商“齊頭并進”,探究構建智能化、數字化時代的協同創新模式。
(本文轉載自環球網)
 手機版|
手機版|

 關注公眾號|
關注公眾號|


 下載手機APP
下載手機APP